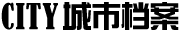风景之外的风景之八十三
行走的铜像
汪兆骞,先前被我称呼汪老。辛丑年,被我称为汪老八十岁的他,迈进了耄耋之年,本应继续称汪老,而我却改了称呼,由汪老而汪公。因我感到称汪老早了些年时。称汪公却能准确地表达我的感情。
此种称呼,是沿袭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人间的雅称,往往是德高望重,于社会有一定分量的文人才能获此称谓。象郭沫若被称为郭公,茅盾被称为茅公。夏衍被称为夏公。内含了一份尊敬的同时,也带了几分亲近。
郭沫若、茅盾、夏衍等被人们尊称为“公”的时候,年龄也只在五十岁上下,皆因了他们文学作品的嗓门高、气场大,有着千千万万的读者。汪公走进八十岁的门槛时,被我称了公,可见了他的不老,亦可见了他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副主编的位置上退休后文学创作上斐然的成就。以及由这成就而给社会带来的文学的良心价值、文学的艺术价值、文学的史料价值和文学的思想价值四重的重量。
有一次聊天时他对我说:“作为人学的文学,检验其文学高下的唯一标椎,就在于其对人性探究的层度。”当他重新捡拾起上个世纪文化界的那些民国大师们的点滴,重新去审视了他们后,在他种着花草冠城南园的小书房里,他从他们的人性,甚至是另一面的人性的“层度”和他们对话,剖析着他们,解读着他们。于是有了用《左传》笔法,写出了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和文化品格煌煌七卷的巨著——《民国清流》系列。
读汪公有着历史良心、文学良心、文人良心至情至性,弥补了文学界最重要、最关紧的被有意遗忘的文学史上的大窟窿、将这些大师们人性还原的《民国清流》系列,不由使人心底渗血。心头总有一根很细的线,下头坠着一个很重很重的秤砣,不知在哪一刻秤砣就会断了线而砸向心底。文人的“独立”何其难!“自由”又何其难!
有关文学、有关日常的生活,我们不时地有微信的交流,我曾写诗赞他:“德邵品高精神气,超尘逸韵魏晋风。”
他回说:“好诗,夸得我心跳脸红。苍老的浮云,能掉几滴干净的水而已。”
我说:“汪公掉下的几滴干净的水,足现了历史和时代的清流。
有一天,汪公又发来一个链接,是他对一位书法家朋友书法艺术的赏析,并附有短短的一句话:“写了篇书法评论,请牧夫指正。”
读后,我还是被他的文字中流溢着思想的神评折服了。
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读您《襟抱兰风的文化坚守》书法评论,再观李多宽先生书法,您的‘空灵如水,静默有禅’将多宽先生的书法精骨点透,使人一下子与多宽先生的笔墨有了感情的交流与融汇。此,皆出于您‘唯能立意,方能造境’的慧眼——略形而神评。”
中国现代的文学界幸有汪公“唯能立意,方能造境”的慧眼,使一大批沙漠里的金子发出了耀眼的光芒。才使中国现代的文学界有了更多的热闹、煽情和骄傲。在这片土地上,汪公更像十九世纪法国油画家米勒著名的油画作品《拾穗者》中的拾穗者,在一片金色的风光中,发现并弯腰捡起文学界一颗颗金黄的麦穗,或大写意、或小写意、或工笔,使一个又一个的景致成框而出。犹如拾穗者,汪公往往是用弱兵,去破生活的强阵。
您将“文化人格”放大
承接魏晋风骨的劲遒
您——汪兆骞
文坛江湖上的老炮儿
退休后不停歇奋进的孺子牛
给您铸一尊铜像
立在文学界三江的源头
这是2021年的7月底我给汪公写的一首长诗《八O后的老头》中的几句。二个月后的九月底,在网络中我看到了郑瑞勇写的《一位作家的“英雄三岛”情怀》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大嶝希元书院还特意邀请毕业于清华大学工艺美术系、现任福州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当代教研室主任、著名青年雕塑家吴曦煌及其学生兰文斌为汪兆骞老师精心创作了铸铜雕像,与明朝理学名宦林希元、明朝孝烈姑祖郑万娘的雕像,一起矗立在田墘社区的“书香读书公园”。汪兆骞老师的文化理念,也将如同这座雕塑一样长存于三岛”。
二O二一年十月十日于北京一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