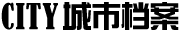宗璞《红豆》,“十七年文学”的一个例外
文 | 汪兆骞
宗璞,原名冯钟璞,是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1938年,十岁的宗璞,随父到昆明,其父在西南联大执教,她入联大附中读书。文 | 汪兆骞
冯友兰教授总是身着长袍,胸前一尺白髯飘飞,有仙风道骨气象,冯先生在中国哲学界享有大名,但其学问和人品一直都存争议。
拙作“民国清流系列”第四卷《大师们的抗战时代》中,专门有一章写冯友兰,名曰:“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尺长白髯飘飞的冯友兰。”
笔者借用唐代卢伦《过玉真公主影殿》诗中的两句,评价并痛惜这位哲学大师。笔者研究并评述冯友兰时,并未想到有一天会评述其爱女宗璞的小说,心情有些敬畏、兴奋。
2001年,笔者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宗璞长篇小说《东藏记》,因书中涉及西南联大的生活,特别感兴趣,那时笔者正在为撰写“民国清流系列”做艰苦的准备。
抗战期间,民国大师会聚西南联大,或执教鞭,或闭门研究著述,或进行文学创作。研究文学史,要遵循《左传》“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掩恶”十二字箴言。
阅读《东藏记》,我特别警惕作者因纠缠私人恩怨而对真相的偏离。即便是小说,指桑骂槐,含沙射影,也伤害小说的艺术真实。比如沈从文的《八骏图》、冰心的《太太的客厅》,多被人诟病。
《东藏记》出版后,引起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的不满,彼此伤了感情。笔者去杨绛家,老人就感慨良多,说1979年,钱锺书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访美,在斯坦福大学参加了该校亚洲语文系的座谈会,应邀发言,谈他的访美印象,后有《钱锺书印象》一书说钱曾在发言中大骂冯友兰云云。
1998年,宗璞撰文,说钱锺书在美骂冯友兰在政治运动中出卖朋友等纯属污蔑、不实之词,杨绛不得不写文澄清钱锺书在美没有说过这类话。
冯友兰乃钱锺书之父钱基博之友,又是钱锺书的老师,杨绛为钱锺书之妻,也是宗璞的老师,这样的关系本不该有这样的尴尬。
据说,冯友兰、钱锺书相继仙逝后,此公案最后由出《钱锺书印象》的出版社向宗璞公开道歉而了结。但从2001年宗璞出版的长篇小说《东藏记》来看,宗璞的心结似并未了结。女儿为捍卫父亲的形象和声誉而战,是很有韧性的,这不奇怪。
宗璞,原名冯钟璞,1928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南唐河。宗璞小时在北京南菁小学就读,抗战时期随父到云南昆明。其父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教书,她在西南联大附中就读。
抗战胜利后,她返回北平,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两年后转入其父执教鞭的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后,她先到政务院宗教事务委员会工作,又到中国文联上班,再调到中国作协《文艺报》《外国文学》编辑部当编辑,后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主席团委员。
宗璞在大学时开始发表作品,但工作后一直忙于工作。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广大文艺工作者解除了思想上的束缚,提高了探索、创造、批评、争论的勇气和积极性。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宗璞以195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红豆》真正踏上文坛,成为一朵“双百方针”催生的艳丽之花。
《红豆》用回首往事的手法,叙述了解放前夕,一对大学生产生了真挚而热烈的爱情,却因各自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而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决裂的故事。
作品以极其细腻的艺术描写,表现女主人公江玫在爱情与革命的选择上,经历犹豫和觉醒,最后走向革命的过程。
江玫从小在温暖的生活中长大,“生活就像那粉红色的夹竹桃一样与世隔绝”。进步女友肖素的影响、父亲精神的感召及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江玫从不问政治到向往并倾向革命,从主持正义到投身火热的斗争,勇敢地奔赴解放战争的战场。
男主人公齐虹,是银行家的公子,他并不是一个纨绔子弟,他爱江玫是真心真意,全心投入,才使他们的爱情缠绵悱恻,矛盾苦涩,“正像鸦片烟一样,使人不幸,而又断绝不了”。小说真切地写出了青年男女彼此相恋时刻骨铭心的甜蜜和伤痛。
《红豆》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知识青年的喜爱,绝不是因为它写爱情,也不完全是因为小说的艺术性打动人心,“而是那种知识分子的个人情感在广大知识分子读者心中所产生的共鸣”。知识分子读者感到一种浓郁的属于自己的气息又回来了。
其实,“未必有人希望强化感情上的留恋而否定两个恋人之间为政治方向不同而做出的选择”(李新宇《“早春天气”里的突围之想——五十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不管怎么解读,《红豆》从思想性、艺术性来看,续接了五四时代知识分子女性如何选择人生道路的主题,独树一帜。宗璞在语言方面的深厚功底与江玫追求人生理想的精神气质融为一体,有一种独具个性的清新高雅的格调。
19世纪以来,知识分子成为世界名著的描写对象。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主要对象成了工农兵,错失了知识分子这一充满文学可能性的题材领域。
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方纪的《来访者》,特别是宗璞的《红豆》,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的出现,给当时的文坛送来一股清新之风,有一种叛逆的味道。
以讴歌革命为宗旨,写大学生投身革命的《青春之歌》,被指责“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进行创作的”(《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
“十七年文学”中,“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越来越敏感,作家越来越难以按照生活的本相及文学原则来塑造自己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回顾“十七年文学”,确实没发现几个可信的真实的知识分子形象,《红豆》是个例外。
宗璞是一位有深厚的学养,有文学创作潜力,有理想,有追求,有个性的女作家。1959年,她到人民公社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创作了反映公社社员生活的短篇小说《桃园女儿嫁窝谷》。
因人民公社本身就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宗璞没有多少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当时全国经济失调,全国性大饥荒已见端倪,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
20世纪60年代伊始,宗璞不得不回归书写她熟悉的知识分子生活。她当然知道,写知识分子越来越敏感。
她创作的《知音》《后门》《不沉的湖》这些带有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代印记,表现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和人生选择主题的作品,把知识分子都写成经过彷徨,最后走向光明大道者,无甚新意,那是时代的局限。
纵是满腹经纶,手有生花妙笔,她也只能收敛了锋芒。正是“自是不开开便好,清高从未合时宜”(张问陶《梅花》)。
新时期是作家真正的春天。20世纪50年代中期,“双百方针”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生气,但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是改造团结的对象。
“文化大革命”中,文学只有八个样板戏。改革开放推动了思想解放,文学也得到解放。此时,蓄力而发的宗璞们,成为文坛最为活跃的作家。
1979年,宗璞以短篇小说《弦上的梦》强势出现在文坛,摘下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桂冠。接着,宗璞推出中篇小说《三生石》,又荣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乘势而发,其《心祭》《鲁鲁》《米家山水》《熊掌》《核桃树的悲剧》《我是谁》《泥淖中的头颅》等小说纷纷亮相,可谓“落日千帆低不度,惊涛一片雪山来”(李攀龙《送子相归广陵》)。
其《弦上的梦》,写知识分子乐珺、梁遐等人,他们即使在逆境生活中被撞得遍体鳞伤,也绝不放弃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即便饱经命运忧患、生活折磨,仍执着于美好的人生信念。
其《三生石》里的梅菩提和她“三生相知”的恋人方知,不管在怎样的逆境中,仍具有屈原式虽九死而无悔的“兰气息,玉精神”。
其《我是谁》描写从海外归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的学者韦弥,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无数次残酷斗争,在生命弥留之际,精神恍惚,仍然不愿变成不齿于人类的虫。
这种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守,给读者留下太多思考的东西。上述小说有诗的意绪、情感,将老庄、现代白描与象征融为一体。
纵观新时期摆脱文化专制禁锢的作家可见,宗璞不像卢新华的小说《伤痕》那样,而是重视呈现原生态的血泪悲剧,真正塑造人物形象的悲剧命运和灵魂创伤,深层次地揭示文化专制的问题。
宗璞新时期的小说在精神和文化层面上与“五四”文学传统衔接和契合,是将世界文化精髓与中国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文化景观。
这与宗璞出身文化世家有关。其父冯友兰乃中国哲学家,称得上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姑母冯沅君也是一位作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创作了小说《隔绝》《隔绝之后》,还是一位研究古典文学的学者。
文化世家家学的濡染和继承,加上又专修过外国文学,兼收并蓄,为宗璞创作独特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创造了条件。
所以,宗璞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蕴藉,又汲取了西方文学作为“人学”的精神。孙犁先生在《宗璞小说散文选·代序》中评价宗璞的文字:
明朗而又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细节。每一句的组织,无文法的疏略;每一段的组织,无浪费或蔓枝。可以说字字锤炼,句句经营。
除了小说,宗璞的散文也写得精彩,比如20世纪60年代写的《西湖漫笔》,80年代发表的《废墟的召唤》《哭·小弟》《霞落燕园》等,后皆结集为《宗璞小说散文选》。1996年,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时,将《三生石》《风庐童话》《丁香结》《熊掌》收入。
1985年以后,宗璞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野葫芦引》。1988年,其第一部《南渡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小说叙述了北平沦陷时期一批文化大师及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际遇,概括了那一代知识分子为国救亡而牺牲一切的浩然正气。
前文提到的《东藏记》,系《野葫芦引》第二卷,于200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总编 杨东志)